大廈衛斯理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衛斯理寫的 大廈(衛斯理小說典藏版17) 和衛斯理的 大廈(衛斯理故事珍藏版)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明窗出版社 和明窗出版社所出版 。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朱嘉雯所指導 吳信杰的 倪匡「衛斯理系列」小說中的靈魂書寫 (2015),提出大廈衛斯理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倪匡、衛斯理、科幻小說、靈魂、腦電波。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劉紀蕙所指導 張智琦的 殖民主義、冷戰經驗與烏托邦書寫:倪匡《衛斯理系列》的再現政治 (2015),提出因為有 衛斯理系列、倪匡、殖民主義、冷戰、香港歷史的重點而找出了 大廈衛斯理的解答。
大廈(衛斯理小說典藏版17)

為了解決大廈衛斯理 的問題,作者衛斯理 這樣論述:
一幢高級摩天住宅大廈,剛剛落成即吸引絡繹不絕的買家參觀,包括大偵探小郭,連身為好友的衛斯理也一起去湊熱鬧。 怪事就在參觀大廈時發生了——人進了電梯,想到二十二樓去,可是電梯卻不斷向上而升,向上升…… 然而,更不可測的事卻接踵而來,有人失蹤,有人斃命……身在案發現場的衛斯理,冒着人間蒸發之險追查到底,大廈的秘密即將揭開﹗幻想小說中的情節,和現實生活中常見的行動結合在一起,給以新的設想,特別是能使看小說的人感到震撼。像乘搭電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幾乎人人,天天,都在進行,誰也未曾想到過那種平凡的行為,有時也可以變得十分可怖﹗——倪匡(衛斯理)
倪匡「衛斯理系列」小說中的靈魂書寫
為了解決大廈衛斯理 的問題,作者吳信杰 這樣論述:
自古以來,靈魂一直充滿著神秘的色彩。就算靈魂雖然在宗教、文學、醫學、哲學、心理學等不同領域中持續著被探討、研究,但這些高科技的現代化研究仍然無法洞悉靈魂的全貌。 倪匡從七〇年代開始創作「衛斯理系列」科幻小說,他融合了傳統文化、宗教、哲學、神話以及現代的科技、對未來的想像,並且加入外星力量作為其靈魂觀點的證明,使得倪匡的靈魂書寫更為豐富與生活化。 倪匡主要的靈魂書寫有二個,其一為宣告外星生命的存在,其二為靈魂即為腦電波。以這兩點為根據,在故事中發展出預言、果報、靈魂出竅、陰間、轉世、改變生命形式、複製身體、複製人、思想控制、存取、合成、成精、變人等靈魂模式。倪匡也結合了中國
傳統靈魂觀念、現代科技以及未來世界。這是在西方科幻小說上甚少見到的。 在靈魂書寫的歷程上,倪匡並未在一開始就明確寫出「靈魂」、「鬼」等類似字眼,而是注入了外星力量、生命科技等科幻成分,十幾年之後,才開始書寫靈魂出竅、轉世投胎等題材。 就算如此,倪匡在創作初期就確信靈魂即為腦電波。人可以見到鬼,或者靈魂有投胎、轉世、出竅等動作,是因為腦電波可以被發送、接收、取出、存入、增強。透過這樣的設定,倪匡式的科幻才如此兼具傳統與科技,進而使小說呈現精彩豐富的內容。
大廈(衛斯理故事珍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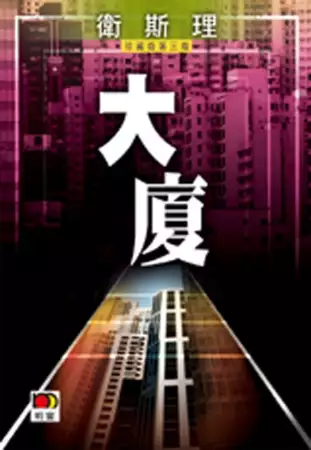
為了解決大廈衛斯理 的問題,作者衛斯理 這樣論述:
一幢高級摩天住宅大廈,剛剛落成即吸引絡繹不絕的買家參觀,包括大偵探小郭,連身為好友的衛斯理也一起去湊熱鬧。 怪事就在參觀大廈時發生了--人進了電梯,想到二十二樓去,可是電梯卻不斷向上而升,向上升…… 然而,更不可測的事卻接踵而來,有人失蹤,有人斃命…… 身在案發現場的衛斯理,冒著人間蒸發之險追查到底,大廈的秘密即將揭開! 幻想小說中的情節,和現實生活中常見的行動結合在一起,給以新的設想,特別是能使看小說的人感到震撼。
殖民主義、冷戰經驗與烏托邦書寫:倪匡《衛斯理系列》的再現政治
為了解決大廈衛斯理 的問題,作者張智琦 這樣論述:
《衛斯理系列》是香港作家倪匡最著名的連載小說,從1963年開始在《明報》連載,直到2004年發行最後一篇小說為止,倪匡一共創作了一百四十五篇小說。1980年代以來,《衛斯理系列》風行香港和台灣等華人地區,被視為是「華文科幻文學」的代表作品,多數研究者也在科幻文類的框架下闡釋小說的內涵。本論文則試圖跳脫科幻的框架,透過歷史化和政治化的視角重新闡釋《明報》連載時期(1963-1992)的《衛斯理系列》,一方面將小說文本連結倪匡的生命經驗,一方面參照香港歷史及社會文化脈絡,試圖探究英國殖民和國際冷戰的雙重歷史背景,如何影響、形塑《衛斯理系列》的文化想像和意識形態,而《衛斯理系列》又如何展現出足以挑
戰和顛覆既存體制的政治意涵。本論文發現,《衛斯理系列》和殖民主義、冷戰有極其錯綜複雜的關係,小說不但承繼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想像,也反映出「勾結式殖民主義」的香港社會文化形構;另一方面,《衛斯理系列》也呈現出香港人獨特的冷戰經驗以及「親英美、反共」的意識形態。儘管倪匡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制約,他在小說中仍對殖民體制和冷戰意識形態有所反思和批判,更通過烏托邦的書寫模式,將建立理想的人和社會的希望寄託在小說中,從而為殖民/冷戰時代下的香港人開闢了一個超越既存體制、充滿可能性的想像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