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程騫寫的 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時窮節乃現 和RobynVanEn的 種好菜,過好生活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時英 和商周出版所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陶儀芬所指導 張珈健的 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2008),提出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金融改革、網絡化金融統御、組織一致、派系制衡、獨立、自律.。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所 顏尚文所指導 楊書濠的 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 (2008),提出因為有 佛教、中國佛教、中國佛教會、人民團體、台灣佛教的重點而找出了 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的解答。
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時窮節乃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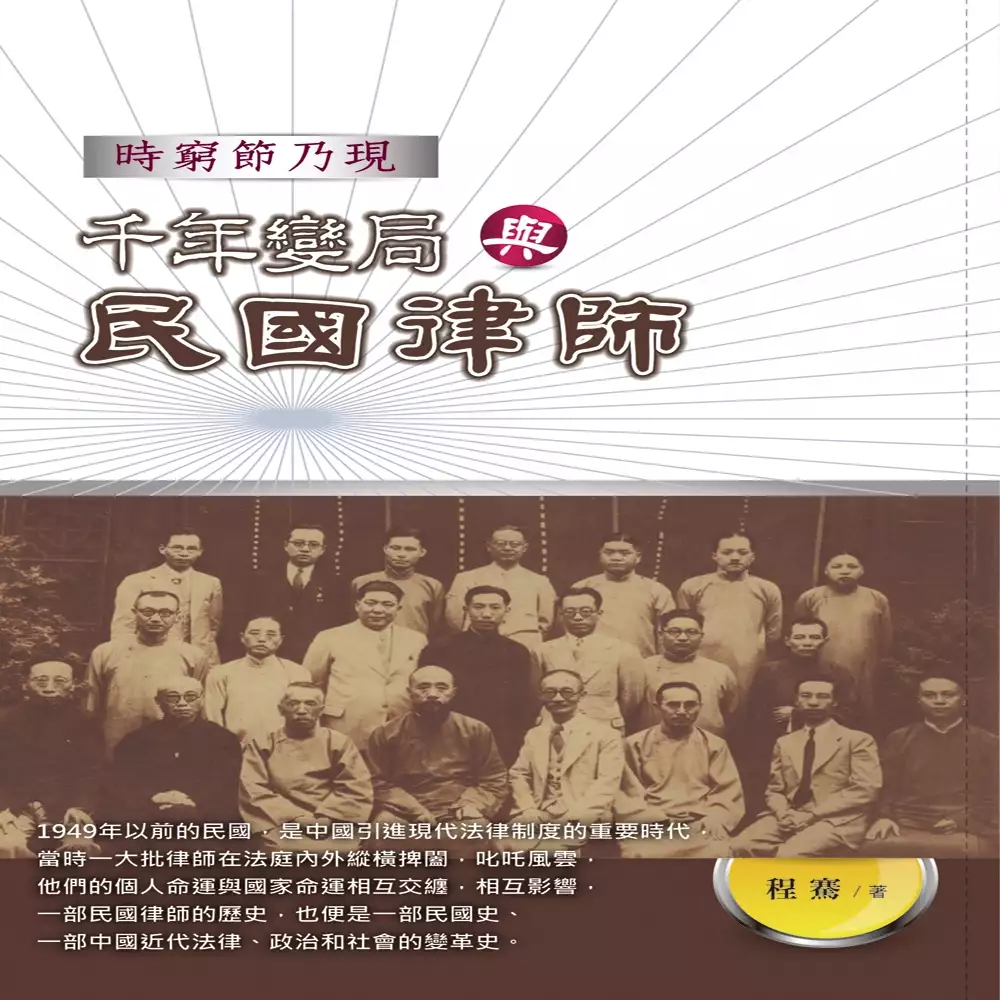
為了解決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 的問題,作者程騫 這樣論述:
近年來,海峽兩岸皆對律師典範與制度發展分作宏觀的疏理。台灣代表作是2005年5月出版的《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此書指出台灣律師制度的兩 條軌跡,一為日治時期律師制度建立(葉清耀律師與蔡式穀律師為中心人物),二為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歷經長期戒嚴的萎縮與解嚴後(1987年起)的蓬勃發 展(林敏生律師與陳傳岳律師為中心人物)。 程騫博士撰寫的《時窮節乃現-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可謂是中國大陸有關律師制度發展 的力作之一。不衹在中國大陸勢將興起傳誦的熱潮,對台灣讀者也是一本可讀性頗高的好書。本書文筆流暢,敘事完整,對民國律師的介紹引經據典,深入淺出,是 一部有關
律師風雲人物的傳記文學,也對律師自治等議題有所探討。 本書從華人律師鼻祖伍延芳與中華民國第1號律師曹汝霖開頭,中間 伴隨精彩的言論自由案件與政治爭議案件,娓娓道來林百架律師為《民國日報》、章士釗律師為《陳獨秀危害民國案》、張耀曾等律師為《七君子案》辯護的始末。 章士釗大律師以嚴格區分言論與行為,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等理論為政治立場不同的好友陳獨秀辯護,被東吳大學法學系選入教材。上述案件對民國憲政的發展與 律師實踐公理正義,皆係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 本書亦介紹五四運動中,劉崇佑律師如何為學生周恩來等辯護,工運律師施洋為漢口 罷工案被捕而從容就義的事蹟;培養司法官聞名的朝陽
大學創辦人江庸律師代理案件,興辦教育與領導律師界的經過;民國時期律師組織以上海律師公會為中心,其 領導人物陳霆銳律師推動撤銷領事裁判權,為會員伸冤、維護律師權利、促進司法公正與建立法律扶助制度,此在今日仍為海峽兩岸律師繼續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 而陳律師除在律師界執牛耳外,其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皆任教東吳大學法學院,春風教化,惠澤學子。另一綻放異彩的為吳經熊律師,吳律師學貫中西,任教各大法學 院,師友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德國法哲學家施塔姆勒與美國證據法學者魏格莫,著作等身,聲譽卓越,其擔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推事時,表現司法獨 立,為時人所稱讚。吳氏後入政界,擔任立法委員,為南京國民政府《五五
憲章》起草人,誠為法律人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表率。 另外,第一女律師鄭毓秀(魏道明之妻)、引發律師界集體抗爭的羅文幹律師,為政治案件辯護的吳凱聲律師、民盟中倡議立憲的沈鈞儒律師與為女權發聲的史良律師,皆有大書特書的一頁。 除了對個別律師的行誼為翔實的介紹,本書末三章亦分對律師公會自治、律師收入及律師業務發展之道加以析述。就律師公會自治言,伍庭芳等人師法西方律師公 會自治傳統,建立民主原則的公會,排除國家管控,防止政黨滲透,並以在野法曹自我定位,維護法治與正義。就律師收入言,公會決定最高限額的公費,律師收入 較法官或一般公務員月入高。就律師業務發展言,則強調辦案口碑與人脈
關係,亦有以報紙廣告宣傳者,但律師公會禁止掮客與包攬訴訟的作法。此就今日兩岸律師 制度等相關規章與倫理規範,亦是應加實踐的目標。 程騫博士在本書所介紹的律師風流人物嗣後在海峽兩岸紛在律師界、司法界與學術界各占鰲頭,相關制度亦不因其敘述舊事而失其新意。撫古思今,可謂其命維新。 我們這個國家,至少在兩千多年前,就有法律,有訴訟,可以開庭打官司。但是,卻一直沒有,也不可以有律師。所謂的訴訟,無非是原被兩造,在官老爺面前, 在兩旁皂隸的虎視眈眈之下,各自陳訴自己的理由或者冤屈。然後聽從青天大老爺的發落。如果不服,屁股上先嚐嚐水火棍的滋味。至於現在電影電視上講得神乎其 神的訟師,其
實根本就沒這種職業。被人稱為訟師的,頂多是兼職。而且不能公開露面,老實的,不過代寫訴狀,刁蠻的,則可以給想打官司的人背後出點餿主意。 這樣的人,一旦被官府鎖定,必遭嚴懲。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攬訟詞,挑撥訴訟者,就是訟棍,這樣的訟棍,歷朝歷代,都是要嚴厲打擊的,輕則流放,重則殺 頭。在一個以非訟為道德的社會裡,所謂的訟師,不僅挑戰官府權威,道德上就不正確。 中國的土地上,第一次有律師,已經是民國了。 清末新政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但畢竟時間太短了。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對多數地方而言,僅僅在紙上。刑事和民事訴訟法的確立,也僅僅在發達地區做到了原 被兩造平等地應訴。鄉紳沒法像過去那樣,拿自
己一個名刺,就把欠租的佃戶送官。律師制度,只能等到民國才問世。中國歷史上第一號的律師證,給了曾經在清末 做過外務部左侍郎的曹汝霖。這位在五四運動中,被罵成大漢奸的人,在日本學的是政治。但是,清末新政期間,他卻參與過憲政編查館的工作,翻譯過日本和德國 的法典,也參與制訂了好些中國的新法典。進入民國,一時間不想做官,當律師,也合乎身份。 清末的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一個副部長做了律師,很給律師長臉。以他在官場和司法界的人脈,沒有官司打不贏的。每次庭審,只要他出席,旁聽的法律學生烏泱烏泱的。出了北京,老百姓找他打官司的人跪了一地。用他的話說,人們是把他當八府巡按了。 曹汝霖的律
師生涯不長,很快就復出做官去了。真正領風騷的,是上海律師公會的律師們。做過民國司法總長和代總理的張耀曾,是這個公會的成員,同樣做過司 法總長的章士釗也是。而且,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張志讓這些民國響噹噹的大名人,都是上海的大律師。其中沈鈞儒,清末中過進士。 國民黨當家之後,中國的司法改革,有所倒退。以黨代政的立法院制訂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以及稍後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開了民國以言治罪的先 河。大批的政治犯,就是在這兩個臨時法律之下,被定罪入獄。好多共產黨人,也就是依照這種法律,被定罪,甚至丟了性命。幸好,那時的上海,還有租界,租界 有中外合審的會審公廨。那時由於律師
們的努力,好些革命者,就是在這裡,被無罪釋放了。 當然,1932年被捕的前中共的總書記陳 獨秀沒有這麼幸運。此時的他,已經被他的黨和共產國際所拋棄。但是,一根筋的他卻依然堅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主張,憑藉他那個托派小組織,展開活動。 被捕之後,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當然沒有錢請律師。但是,他昔日的好友章士釗律師,卻自願免費為他辯護。當年章士釗在江蘇高等法院上,為陳獨秀所做的辯護 詞,已經載入史冊了,問世不久,就成了著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輔助教材。看當時報紙記錄的庭審狀況,法官們簡直被章大律師弄得張口結舌,狼狽不堪。儘管, 章士釗的辯論,陳獨秀並不買帳。 同樣難堪的法庭庭審,還
有1936年的“七君子案”,法官在如此強勢的律師面前,簡直就是遭罪。 甚至,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審理漢奸案,也遭遇這樣的尷尬。原本法官們覺得審判漢奸,民眾一定擁戴,所以,特別在朝天門廣場直播。沒想到,由於國民黨 抗戰勝利後,一系列倒行逆施,大失民心,同時,也由於律師們精彩的駁辯,旁聽席上,直播的廣場上,竟然出現了一邊倒——一邊倒向漢奸被告的現象。 然而,不管怎樣尷尬,怎麼難堪。律師們沒有受到刁難,也沒有人想起會把他們驅逐出庭。包括此前的取證,閱卷,會見當事人,都沒有任何問題。儘管民國的立 法機構,炮製了若干完全有違《中華民國約法》精神的臨時法律,作為訓政時期限制個人權利的利器,
但是,從清末傳下來的司法改革成果,卻也沒有被廢止。至 少,律師們能幹活,而且能把活兒幹得相當好。他們中的好多人,過得也相當滋潤,還成了這個國家一等一的大名人。 從清末司法改革算起,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走了一個多世紀的路,讓我這個外行沒有想到的是,律師有的時候,居然還是妾身未明。影視劇視他們為訟師,他們自己有時也自稱“大狀”,民國律師的風光,也許不足以點醒人們,但至少會給我們提供一些耐人尋味的故事。 本書書成,作者和編輯,命我這個外行作序,盛情難卻,狗尾續貂。於是有了上述的文字。
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 的問題,作者張珈健 這樣論述:
本研究嘗試建立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的因果關係,並找出影響官僚自主性的制度性因素,藉此對台灣金融自由化所面臨之危機提出整體一貫的解釋。官僚體系經常必須解決自主性過強或太弱導致的危機,亦即「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於是政經行為者如何處理官僚自主性內在矛盾將直接影響金融改革表現。追求官僚體系內部團結會降低金改政策執行的制衡力量,增加官僚獨斷濫權的風險;強化官僚體系內部制衡時,則相對減少官僚推動金改時面臨外來干預的抗衡力量,提高政策被滲透或扭曲的可能性。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疏離於本土社會,迅速國有化金融體系輔以專制暴力隔絕外在的尋租壓力;另方面則將分屬不同派系的黨籍官僚混編至重要金融及行庫
要職,藉由派系相互監視的機制避免官僚濫權。這種利用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派系關係、外來政權特性所構建的金融治理網絡,亦即「網絡化金融統御」,兼顧官僚體系的組織一致與內部制衡,於焉確保金融官僚既獨立又自律的統理金融改革。隨著冷戰終結、威權轉型,國民黨政府內的主要統治派系在權力繼承鬥爭時,基於政權維繫而選擇鞏固網絡化金融統御的團結,以中常會/黨管會為樞紐凝聚黨、政、商三系一體主導19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組織一致的黨籍金融官僚指揮金改時高度獨立自主,卻無可避免的籠罩於黨國濫權陰霾。拜國民黨內部分裂而在2000年猝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缺乏駕馭官僚體制的經驗於是廣泛結盟外部政、商、學界力量,雖然意外的重現網
絡化金融統御之派系制衡,卻沒有及時演化弭平政策衝突的機制。內部分歧的金融官僚在改革過程經常面臨政令不一致,因而傾向自我約束甚至放棄管理市場秩序,讓金融自由化不可或缺的再管制付之闕如,也就使兩次金改受迫於各方勢力的扭曲與滲透。
種好菜,過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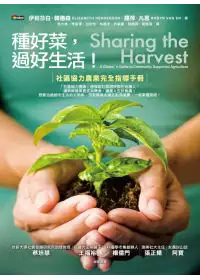
為了解決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 的問題,作者RobynVanEn 這樣論述:
你必須成為改變者,為了你所期望的世界。──甘地 「社區協力農業」對台灣的讀者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在美國卻已推行二、三十年。簡單來說,「社區協力農業」就是社區居民直接購買在地的農產品,尤其支持「力行有機栽培的小農」,分擔了小農的生活風險,讓他們不再因為氣候、市場的變化而影響生計。 當現代人的生活愈來愈都市化,我們在超級市場購買蔬菜、在餐廳吃飯,甚至在超商解決三餐,食物在商店、餐廳,或者販賣機裡出現,食物到餐桌前已經被清洗、處理、包裝,甚至經過放射線照射,並且運送了非常遙遠的路程。我們不再知道自己吃的食物從哪裡來,也不再知道自己吃的食物是不是安全。 而「社區協力農業」正
是直接連結消費者與農人的那條線,在都市的近郊,農人們堅持種植無農藥、有機的蔬果,而消費者甚至可以在假日直接參與種植、採收或是分包的工作。消費者每週都能在鄰近地點收到新鮮、當季的產品,他們會知道,自己花的每一分錢都直接付給種植、照料和收成食物的人們;而自己支持的有機栽培方法,則保護了土壤資源和水的品質,甚至能確保自己的健康。 在美國,已有近1300個這樣的農場為消費者的健康把關。而台灣,這股力量也不斷醞釀,從花蓮的大王菜鋪子、宜蘭的穀東俱樂部、台北希望廣場、漂鳥網,到各地的農民市集;假日農作甚至變成一股潮流,在忙碌的現代社會中發酵。 對於想參與這個浪潮的讀者來說,這是第一本詳細討論社區協
力農業的書,作者分享了各個農場的運作方式、他們面對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當然,作者也分享了每個消費者在參與這個活動中的笑聲與汗水。對於各種都市生活產生的文明病,社區協力農業也許正是維護心理與身體健康的一帖良方。 作者簡介 羅萍.凡恩(Robyn Van En) 在生命中的最後十年專致推廣社區協力農業,她在會議、工作坊中演說,面對面或透過電話給予建議和解決問題。她是北美洲社區協力農業的創辦人以及唯一的專職人員。 伊利莎白.韓德森(Elizabeth Henderson) 整理了全國有關社區協力農業的論文、羅萍的信件,以及時事通訊的影印本,整合成此書出版。
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
為了解決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 的問題,作者楊書濠 這樣論述:
本文的題目〈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研究動機是想要瞭解解嚴前後台灣社會的變化狀況。因為一個國家的戒嚴對整個社會發展,會產生極大的變化,台灣地區更是經歷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為世界各國之最。戒嚴時期的社會型態與民主社會有著極大的不同,因此在面對台灣社會由戒嚴到解嚴的過程中,人民團體所受到的影響與變化,是值得觀察研究的。 在觀察的對象上,諸多的人民團體中,何以會選定中國佛教會呢?主要的原因有下列兩點:一、它是中國最早成立,並且通過政府立案合法的人民團體。民國成立之初,佛教人士即積極的透過各種整合,成立「中華佛教總會」,並分別取得了當時南京政府與後來袁世凱
政權的確認,成為合法的人民團體組織。之後雖然經過多次波折與重組,自民國十八年終於成立了「中國佛教會」。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中國佛教會不僅是戒嚴時期佛教界唯一的中央級人民團體組織,至今在台灣之佛教界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其組織發展的歷史悠久,足以作為觀察宗教與政治互動的對象。二、它是國民黨較早認可的人民團體。國民政府在北伐完成後,進入了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後,民國十九年(1930)中國佛教會即獲得國民黨中央黨部認可,成為國民黨較早給發合法證書的人民團體,與國民黨之間的互動歷史悠久,留下相當豐富的資料可資比較研究。 從戒嚴到解嚴的時間界定上,本文主要以中國佛教會的發展為主體,觀察其在民國六十七
年(1978)至民國九十年(2001)之間的發展。之所以如此界定時間的原因,是因為此段時間正好歷經中國佛教會第九屆至第十四屆會期,分別有白聖、悟明及淨心三人擔任理事長。三位理事長中,白聖擔任理事長的第九屆、第十屆(1978–1986),正處於戒嚴時期;悟明擔任第十一屆、第十二屆(1986-1993)理事長,正是台灣社會處於解嚴前後的敏感時期;淨心法師領導的中佛會第十三屆、第十四屆(1993-2001),則為台灣社會解嚴後,至政黨輪替間的敏感時期。本文即是希望透過中國佛教會在此三個階段的發展,觀察台灣社會從戒嚴到解嚴的過程中,對此一人民團體帶來何種的衝擊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