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曾野綾子寫的 優雅老年的才情 和孫震的 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選譯今釋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社会思潮】个人主义思潮的西方源流——《论个人主义思潮》随札(2)也說明:在社会思想领域,有句口号叫“言必称希腊”。意思是,凡是有点年头的思想理论,往往会追溯到古希腊。个人主义思潮也不例外。 个人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发展可以分为古希腊 ...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天下雜誌 和天下文化所出版 。
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陳中民所指導 李筱媛的 現代台灣單身男女的婚姻觀與「家」的想像-以新竹地區高教育專業工作者為例 (2012),提出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單身、婚姻觀、家庭自我認同意識、家。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何淑貞所指導 黃明誠的 才性情感與玄心--論魏晉藝術精神的內涵與發展 (2003),提出因為有 魏晉藝術、魏晉美學、比較美學、才性、藝術精神、玄學、玄風、玄心的重點而找出了 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的解答。
最後網站人生哲學講義則補充:2.8啟蒙運動時期的人生哲學:接受了不少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見解,主張人性 ... 中國人的祭天、西方人的宗教禮儀)求與天達成溝通;基本上說神對人是全知的,而人對天 ...
優雅老年的才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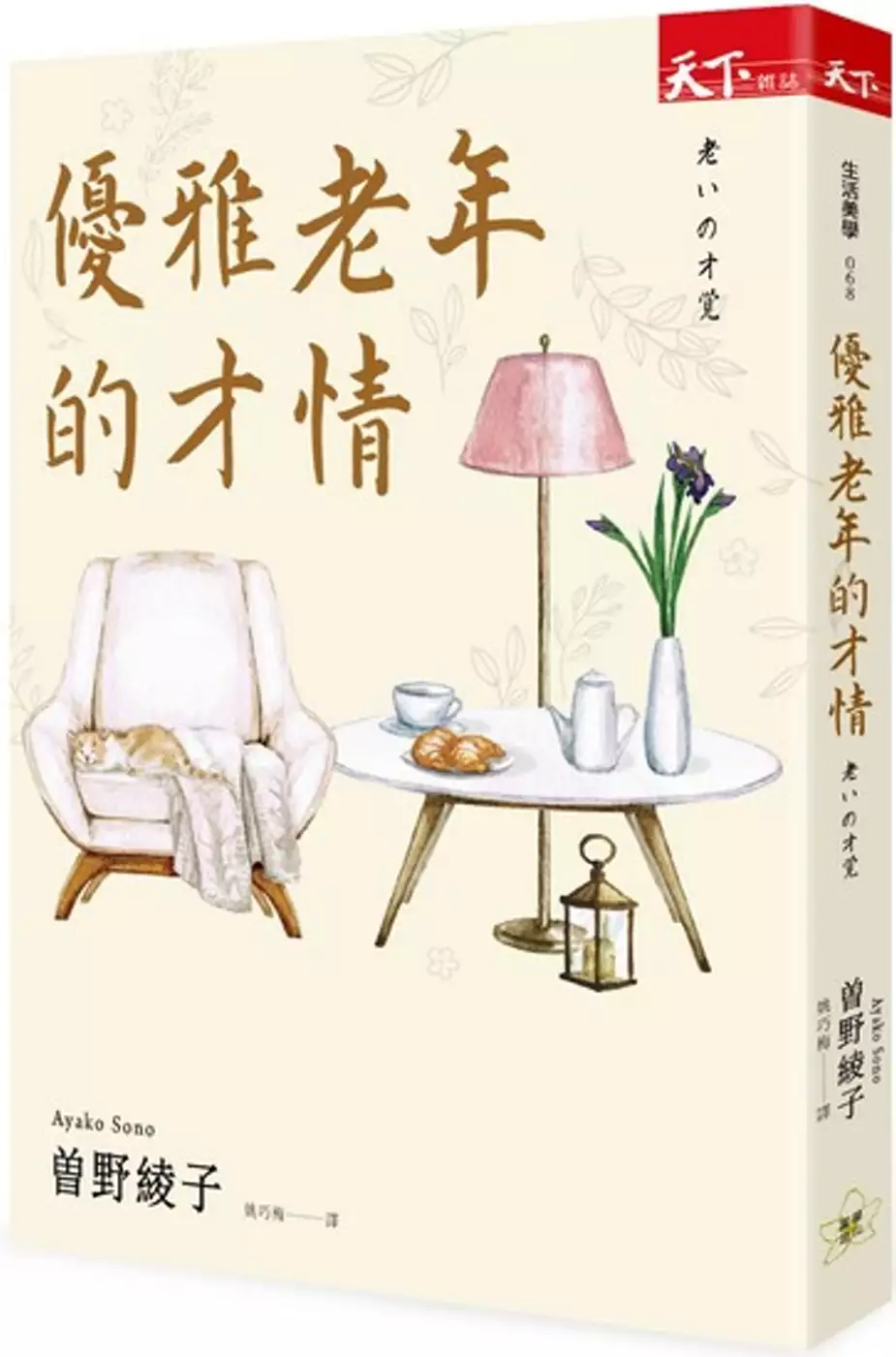
為了解決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 的問題,作者曾野綾子 這樣論述:
少年/青年期是身體的發育期,而壯年與老年則是精神發育的完成期…… 為了對應日益逼近的老境,人人都應要擁有《優雅老年的才情》 改版經典版 日本銷售突破100萬冊 ☆☆☆☆☆日本AMAZON評論3.6星☆☆☆☆☆ 不懂得老年為何物的老人急遽增加 面臨超高齡化時代的現在,任性的老人才是社會的大問題 要了解老年,必須從熟年做起! 日本長青女作家曾野綾子建議:老年後不依賴他人,要靠自己的才情活得有趣! 進入熟年,邁向老年,想要活的長久愉快,應該擁有「七種才情」: 一、「自立」與「自律」 二、到死以前的勞動 三、與夫婦.親子之間的交際 四、不缺錢 五、
與孤獨共生、覺得人生有趣 六、與年老、疾病與死亡可親近 七、擁有神的視點 你怕老嗎?你抗拒老嗎?你不承認老嗎? 日本長青女作家曾野綾子指出,不懂得老年為何物的老人急遽增加,面臨超高齡化時代的現在,任性的老人才是社會最大問題。 面對現代老人逐漸成為「幫我族」、「伸手族」,曾野綾子認為,大家應該要反求諸己,擁有老年的「才情」,成為自立的老人。以前的人,腦中自然地會設想各種情況,然後找到解決的方法。如果這個方法行不通,再思索下一個方法。在腦部如此靈活地運轉下,總會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這就是才情──「我們這一代,自幼即被訓練『要有才情』。任何事情不需一一詢問別人,而是反求諸己,
靠自己的腦力想,這件事該怎麼做才能順利完成。」 能具備「才情」的生活,才能真正快活地度過老年。在《優雅老年的才情》一書中,曾野綾子以自身的經驗,與讀者分享對於「老年」的看法,以及對日本社會「老人」現象的反省。任何人都有機會邁入老年,不只熟年長者、壯年中堅份子,甚至是青年,都能從本書中看到曾野綾子對「自立生活」的感動,不但可做為自身將來臨老的心理準備,更值得大家反思自身的生活態度,啟發生活新美學。 名人推薦 朱為民 老年醫學、安寧緩和專科醫師 江漢聲 輔仁大學校長 李玉蟬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理事長 洪淑娟 及人牙醫診所所長、第一位65歲完登百岳的女醫師 馬大元 身心科
醫師、馬大元診所負責人 秦夢群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黃光國 國家講座教授 黃維仁 美國西北大學臨床心理學家、親密之旅課程創始者 詹志禹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葉雅馨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主任 劉黎兒 兩性作家 薇薇夫人 兩性專欄作家 崔家蓉 前交通大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所長
現代台灣單身男女的婚姻觀與「家」的想像-以新竹地區高教育專業工作者為例
為了解決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 的問題,作者李筱媛 這樣論述:
隨著社會變遷,臺灣男女初婚年齡不斷往後延,年輕世代在生育期間未婚的比率提高,牽動臺灣整體人口結構,進而讓家庭的人口組成產生轉變,改變了家庭歷程。本研究從現階段臺灣社會適婚年齡晚婚的現象,以10位30歲以上單身男性與10位28歲以上單身女性且未曾有過婚姻關係者作為研究報導人,深入訪談現代男女對於婚姻的態度,並透過觀察其日常生活的實踐,以瞭解其對於「家」的想像。本研究發現多數的報導人並不是全然拒絕婚姻,而是缺乏適當的對象,加上受到整體社會環境影響,徘徊在婚與不婚之間,因此想透過單身男女的角度重新看待原有婚姻的意義,並進一步了解適婚而未婚的男女所承受主流社會輿論的壓力。研究訪談過程中,明顯感受到現
代單身男女在婚姻態度、擇偶條件與成家行動上,深受傳統漢人家族主義與現代西方個人主義的拉扯而擺盪,努力想從其中找尋維繫傳統家庭文化的理想與現代個人自由空間的平衡點,認為不為「成家」而「成家」,反而更能找到屬於自己人生的幸福。婚姻既是生育子女的重要條件,也是家庭的源頭,婚姻態度的改變也影響著現代男女對於「家」的概念。婚姻(特別是初婚)又與生育有著密切關連,現代單身男女不婚、晚婚的現象,引發一波人口結構與家庭危機論,讓人不得不思考究竟「家」的定義和條件為何?為了更貼近分析歷史轉折時期的家庭狀況,本研究採取上野千鶴子的家庭自我認同意識(Family Identity FI)這一操作性概念,來掌握當代臺
灣家庭結構的變化,因此本研究透過訪談單身男女家庭自我認同意識與觀察其居住型態和原生家庭成員的互動以及單身獨居空間的規劃,來呈現更多元且動態的家庭形貌。
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選譯今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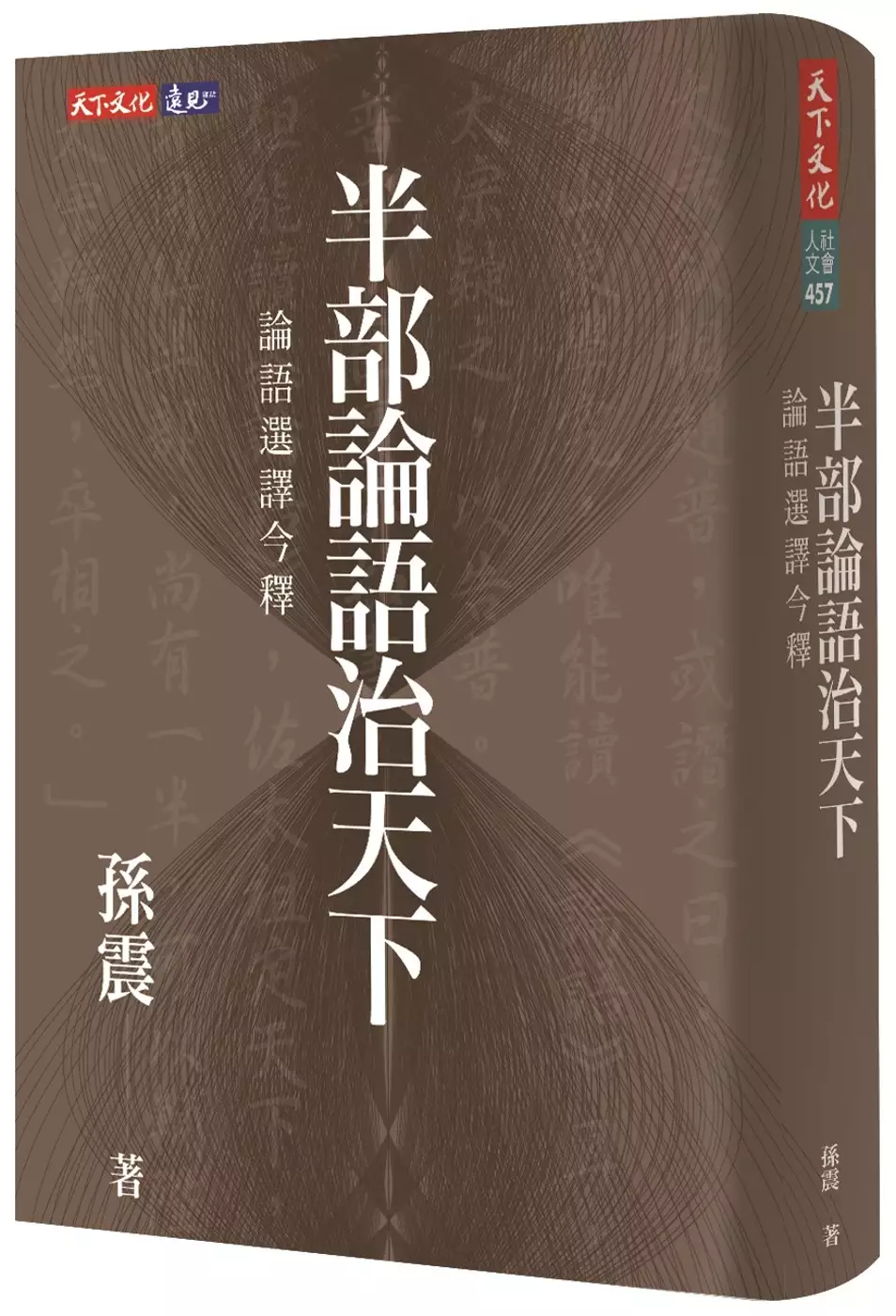
為了解決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 的問題,作者孫震 這樣論述:
科技不斷進步,解除大自然給我們的限制;經濟不斷成長,解除物質給我們的限制;管制不斷放寬,解除制度給我們的限制。我們不思節制,為所欲為,一步一步將世界推向懸崖邊緣。 歷史的發展雖然屢次背離孔子的思想,然而終須回到孔子指引我們的道路,世界才有永續發展的可能。――孫震 《論語》是儒家思想的經典,是至聖先師孔子與其弟子的答問錄,記載了關於「仁」與「倫理」的各種智慧。宋朝開國宰相趙普各以半部《論語》,助宋太祖及宋太宗平定、治理天下,故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古代中國社會處於停滯經濟時代,政府依靠禮制安定社會秩序,倫理在此時發揮重要作用;現代社會的成長經濟型態
帶來便利生活,卻也因個人欲望過度擴張,造成傷害他人利益的事件層出不窮。利己與利他的界線失去平衡,大同社會的理想愈來愈難實現,令現代社會發展陷入不安。 《半部論語治天下》是中國文化精髓的集結,是儒家思想在現代的重新詮釋。前台大校長孫震以經濟學者的角度,利用古人的智慧解決當前社會各種難題,找出未來世界的運行法則――在物欲與自我利益高漲的當代世界,仁慈和倫理並非陳舊的觀念,只要回歸孔子指引的方向,地球就能永續發展。
才性情感與玄心--論魏晉藝術精神的內涵與發展
為了解決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 的問題,作者黃明誠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研究的目的,在立基於現代學術的基礎上,反省研究中國傳統藝術論及其背後的思想基礎、價值論以釐定藝術創作的根源,瞭解藝術創作所從出的精神內涵;並藉以理解魏晉藝術精神之內涵,進而探討中國藝術精神的根源及其在魏晉時代所呈現的風貌;復進一步探討魏晉藝術自覺的時代背景及緣由,並確認魏晉藝術精神與中國傳統生命哲學與藝術精神的關係,和它在中國藝術發展史的地位與影響。 本論文名之為《才性、情感與玄風──論魏晉藝術精神的內涵與發展》,是指所謂魏晉藝術精神的內涵就在才性主體、情感主體與玄學人格三者所構成的人格精神,而此人格精神正是魏晉藝術創作的根源,也因為有此人格精神的覺醒,魏
晉藝術乃呈現其不同於先秦兩漢的風貌,才性、情感、玄風三者所交融而成的有機整體人格層面,正是所謂「魏晉風度」的精神內蘊。 我們若將東漢末年至東晉這一時期視為一文化史研究之斷代,實可見出整個時代藝術精神的發展變化與士人如何尋求生命歸宿的心靈演變史。後起的南北朝,甚至更晚的唐、宋、元、明、清的許多藝術理論、士大夫生活情調與審美品味,都與這時代所奠下的士人人格心靈基型有關。魏晉時代不只是中國哲學發展的突破階段,也是藝術發展的重要時代,許多美學理論、藝術理論,諸如書法、音樂、詩文、繪畫的本體論、創作論、形式論、鑒賞論都得到某種程度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中國士大夫的一些藝術品味、審美趣
味及生活情調都與這時期所奠下的基礎有關,諸如重雅輕俗,強調士人有別工匠庶人的審美趣味,重神輕形、重意輕言,自然任真、適性任情、表現自我、放情山水等美感品味、生活趣味都在此時期得到明確的行為實踐和理論論述。因此,魏晉時代確實是研究中國藝術精神特性的關鍵時期。 相較漢代文化,魏晉有一明顯的「文化轉向」 :由經學轉為玄學;由宇宙論轉向本體論;群體生活轉向個人生活;外在政治世界轉向內心感情世界;道德律令轉向藝術情調;德性論轉為才性論、情感論;建功立業的價值追尋轉向人存在的悲劇性處境省思。此時代精神與漢人相較恰為反差:漢人一派厚重、樸質、博大、篤實的儒者氣象,強調尊天崇聖、克己復
禮、通經致用,在大一統的制度下整個社會凝結、堅固,士人克盡職守,捍衛三綱五常,扮演忠臣孝子之角色,最後卻流於僵化閉塞的名教。而魏晉人則卸下國家沉重的責任感,脫掉禮教緊密的束縛,精神轉為輕靈、疏朗、飄逸、清新、脫俗的藝術情調,悠游於人世宴饗之樂與山野林園之趣,名士風流的神韻,是追求自然,率性任真,最後卻流於淺薄放蕩,以悲劇作收。 彷彿印證了德人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西方的沒落》中所主張的,文化有如生命體,自有其生、老、病、死的生長規律之文化有機論。當我們深入魏晉文化的底層,也宛如聆賞一首生命的樂章,其中有歡愉、瀟灑、輕靈、飄逸的節奏,也有感傷、苦痛、抑
鬱、悲愴的曲調,這是魏晉文化的二重奏,也說明了古往今來生命存在的底蘊。 現今學術界研究魏晉藝術史,有些看法幾乎已成定論,諸如:魏晉是文學自覺、個體自覺、美的自覺與藝術自覺的時代;魏晉在哲學與文學、藝術上創造了重大的成就,開啟了一個新的里程碑。而探討這種現象的成因,有兩個常見的解釋:第一、認為導因於時代混亂、政局動蕩、天災人禍相尋及大一統儒家思想的崩解等社會因素所帶來的價值混亂、人心迷惘,繼而引發存在意義重新認可、追尋的活動,並由此興起個體自覺思潮。第二、認為魏晉以後的門第文化及莊園經濟形態,使得此時的士大夫更有餘暇、餘力及文化資源去從事藝術創作,乃至藝術化的生活追求。
這兩種解釋都是偏於藝術興起外緣因素的解釋,如果我們由文化社會學來看,精神宛如一顆種籽,如果時代背景、經濟因素、學術環境所構成的文化土壤合宜,種籽自然就容易開花結果、枝繁葉茂。魏晉的時代氛圍無疑為藝術精神種籽的成長茁壯、斑斕映發提供合適的環境。因此這兩種解釋自有其合理性。但如果由人內部的精神層面及整個藝術動力論的角度,進一步探討個體自覺與整個魏晉時代藝術自覺的關係,可發現因為個體自覺,所以珍視個人存在的獨特價值,並藉由藝術創作及表現個人獨特形貌精神所流露的美來肯定自我,尋求認同,自我實現;而且試圖為人的精神本質作哲學本體論的闡述,以確立人存在的獨特性及價值依據;加上起於漢末的
人物品鑑之風及繼起的才性理論,更助長這股個體自覺的思潮。 但進一步詢問個體自覺的精神本質為何,其實就是一種懷疑權威,肯並自我獨特情感、思想,尋求生命創造實踐與存在意義確立的精神。我們可以確立這種尋求存在意義的精神乃是出於人的天性,也是人有別於其他動物的特質,只有人會為存在的意義所苦,其他的動物只要能夠生存即可,但人除了活下去外,他還會要求存在的意義,因此只有人會思考生命的意義,「人為什麼而活」乃是生命的終極問題,也只有人會為追求存在意義而從事文化的創作。而藝術就是一種人存在意義的詮釋與實踐的特殊活動,透過藝術,人表現了人對生命的理解與價值的渴望。可以說,強烈追求存在意義、尋
找自我精神的皈依其實就是一切藝術創造的根源,藝術是作為一種存在意義貞定的感性形式而確立的 。就此而論,漢末以來的藝術自覺就具有藝術學的普遍性價值,也有了作為研究人類心靈史之精神現象學價值。 魏晉承漢末大亂,面臨的是一個「價值重新評估」的時代,過去大一統政權下,儒術權威所提供的價值信仰系統面臨崩解,昔日許多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物開始面對質疑,朗朗乾坤下,所謂的天道、天理彷彿都已消失,「人活著是為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自己獨特的生存價值為何?」成為士人心中所亟於解答的終極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歸結為「人是什麼?」的永恆之謎,人不只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形而上學的動物」
,他更是尋求意義、建構意義的動物,而這正是人類文化創造的終極動能。許多魏晉文化活動都是對這類問題的反思與回應,不同反思與回應形成不同的世界觀、價值信仰、意識型態,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信仰、意識型態又進而變成不同的生活行為、行動模式。魏晉士人面對此問題時,或在哲學的思考中建構一種逍遙自在、不受塵垢污染的精神樂土,追求與道合一的玄冥之境;或飲酒服藥,尋求自我麻痺,享受瞬間的歡娛;或者乾脆承認這個世界是無意義的,沒有來世,人沒有什麼形而上的事物值得追尋,只有「此在」才是可把握的,只有盡情的享受目前,才是永恆,笙歌達旦、縱情女色,任誕乖違、行為張狂,這些行徑都可以在魏晉士人身上發現,也成為後世對魏晉典型
士風的認知,某些史家也因此視魏晉為一個頹廢墮落的時代。但是這個時代,也有一群敏感的靈魂,不相信生命這種永恆的沉淪,他們相信有些東西可以令他們不朽,令他們的生命得到安歇,讓靈魂不再流浪,不再孤苦無依,生命的意義在這裡可以得到貞定,這就是宗教與藝術。 魏晉士人有人走向宗教,佛教在此時於中國本土落地生根,絕非偶然,它反映魏晉士人對存在迷惘的恐懼,他們希望進入一個無生無死、無思無慮、無苦無悲的涅槃境界,或超越現世此岸之痛苦,進入彼岸之淨土。也有人走向藝術,相較宗教所提供的精神慰藉,這些人不免有「佛道言人死當得復生,僕不信此之審」、「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牟子理惑論
》)的迷惑,他們不相信人可以無思無慮、無苦無悲,只有情感、只有具體感受到的生命才是其存在的本質,因此這些士人有了「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的存在自覺,他們毋寧相信只有藝術才能使精神不死,藝術可以把他們的迷惘、痛苦、血淚化為一種美的形式,使他們的生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這個世界,魏晉時代的許多詩歌只是純粹的眼淚,「就像玫瑰花從有刺的灌木裏生長開放一樣」 ,生命的苦難悲愴變成這些詩歌所以產生的土壤,他們在苦難中歌唱,用歌聲安慰別人,也安慰自己。透過藝術,彼此的苦難有了傾訴的管道,生命在這種藝術的觀照與理解中,遂有了交流的可能。 魏晉藝術的興起就是源於一種價值信仰失落的痛苦與解
脫,這種信仰失落迷惘的痛苦愈劇,那種藝術的創作之火愈是熾烈,魏晉可說是集「美麗與哀愁」於一身的時代,士人沉溺於存在的憂鬱中,深刻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性及存在的悲劇境況,在痛苦中,如春蠶吐絲,作繭自縛,最後這些痛苦的糾纏終於化為藝術的彩衣,成為中國藝術史動人的形象。魏晉這種因為痛苦、徬徨、迷惘而生個體自覺,遂演成藝術的自覺,人的自覺與藝術自覺雙軌並行,可以說魏晉士人是先發現了人,才發現了藝術,因此人性論與藝術論是基於同一種思想的觀點而提出,許多人物品鑑的觀念也被用於藝術論上,對魏晉士人而言,藝術是人格的延伸,是人格的實踐,藝術論就是人論,最高的藝術就是自我生命的符號形式實踐。
人格美、才氣美、情感美、智慧美、生命美等內在美和流露於外的風姿美、文采美、藝術美,遂成為魏晉士人自我實踐和克服存在憂鬱的憑藉,成為痛苦的慰藉,寂寞的依靠。魏晉士大夫以表現個體之美贏得士階層尊重,並藉由藝術才能的展現,作為晉身更高階層的手段 ,因此藝術的地位遂由傳統工匠的地位,提升為士階層交往的社交工具,詩歌、書法、繪畫、音樂、論辯等成為表現自我生命獨特風姿、價值的客觀化活動。因此,藝術可說是當時士人自我實現、自我肯定的一種生命的實踐,也是為了滿足自我心靈的高層需求。魏晉美學遂以一種有別於西方純理論邏輯型態的美學出現,其重心乃由士人對生命的本質出發,將此生命體悟化為的美的感性形式,可說是一種生
命的藝術化描述,此乃一種生命美學的型態,即將生命視為藝術創造的根源,最高的藝術就是生命本身,就是自我的人格,藝術美是人格美的對象化,藝術就是自我生命的實踐形式。 魏晉這種生命藝術化、藝術生命化的美學型態,其終極意義在確立生命意識的表現與形式化實踐乃是體用關係,人格為體,藝術形式為用,用因體發,體因用顯,藝術成為自我精神生命的留存與人我生命交流的憑藉,因此本文反對將魏晉時代的美學比附西方「為藝術而藝術」 的思潮,因為魏晉藝術的終極目標其實指向生命的表現、交流與安頓,所以魏晉藝術家對「知音」的渴望是極其強烈的,也強調藝術形式所表現的風格與自我生命型態是合而為一,形式美即生命美的
表現。這種生命美學當然有別於先秦德性生命的美學型態,而偏重於感性生命、氣質材性的自然流露,遂成為中國生命美學的兩種型態。中國藝術的核心恆指向人的生命存在,而與西方強調技術法則、邏輯形態、客觀結構的美學形成強烈的對比。 魏晉被視為中國藝術自覺的時代,已漸漸擺脫道德教條的束縛,重視「純藝術」的觀念,對藝術形式美的規律及藝術技巧、法則的探討,都較先秦兩漢更為細密深入,但其中心思想仍然強調藝術本源必須是某種超越技術層面的精神事物。魏晉思想家在人的道德人格之外,發現了人的氣質、才性、情感、玄風的主體人格,並將此種才性人格之美視為藝術的本質,使藝術開始擺脫道德教條的束縛,與人內在的
真實生命取得更緊密的關係,曹丕《典論.論文》的「文氣論」,在先秦兩漢的氣化宇宙論及人物品鑒之學的基礎上,畫龍點睛、千里來穴,精確地點出藝術與主體生命之關係,從此文氣說成為中國藝術思想的中心議題,貫串每個時代每個藝術項目。而當時的才性論代表作品──劉卲的《人物志》開宗明義就說:「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九徵第一>)他所謂的「情性」雖然亦包涵道德的內涵,但本質上其實是一種天生而就、不可學、不可改易的才性氣質人格,而人的才性氣質常表現在外貌舉止和不同的情感模式上,所謂「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同上),劉昺的注就說:「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神見貌,形驗有九」。不同情性的主體對客體世
界的理解感受也就不同,形諸於藝術形式時也就化為多采多姿的藝術形貌。人的動作、形貌、穿著及生活,就現代藝術的觀點來看,也是藝術的一個項目,所謂「行動藝術」、「身體藝術」即以行動及身體為符號媒介去表現主體對世界的詮釋與自我獨特的生命觀照,因此人本身的行為生活就是現代藝術研究的一個領域,日本三島由紀夫就曾說過:「我的作品就是我。」 魏晉時代的才性論及當時的人物品鑒之學,雖未以現代的術語道出這種看法,不過在其論述中,即將人體容止、形貌、風姿視為藝術而加以表現,魏晉名士致力將生命藝術化,將生活藝術化,將身體視為藝術加以表現,觀者也將其視為藝術品加以品味欣賞。中國的美學與這種人物品
鑒之學息息相關,學者甚至以為中國美學出發於人物品藻之哲學,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就發源於人格美的評賞 。可以說,中國的藝術論的核心是建立在人學之上,藝術學即人學,因此要瞭解中國藝術思想之發展,必須瞭解整個人格美的內涵的變化歷史。 魏晉藝術思想的核心就產生自當時的人性論及藝術主體精神內涵的思考上,陸機的《文賦》強調為文之「用心」,強調「詩緣情而綺靡」,劉勰《文心雕龍》則說:「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體性篇>)他們皆將主體生命力所表現出的性格、氣質、情感視為藝術的本源,也是決定藝術風格的主要因素,不同的人格氣
質表現出不同的情感反應,形成對世界不同的觀照態度,也就表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因此主體人格是一切藝術創造的核心,也是藝術鑒賞的關鍵。這時代的藝術創造論或藝術鑒賞論都將討論的中心置於作者的主體人格及心理、情感反映過程上。 中國思想強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傳.繫辭上》語)、「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認為藝術創作最重要的是「匠心獨運」,「畫要吾自畫,書要吾自書」 ,相傳為王羲之所寫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也說:「夫紙者,陣也;筆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揚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他認為書法之所以成為藝術,在於超越點畫等技術層面的「藝術性」特質,而此「藝術性」特質乃源於創作主體獨特的審美意念,隨意所適,主體的「心意」才是書法藝術的本體。書法發展伊始,雖強調用筆的技術與書體之勢,因此有許多論「筆勢」的書論產生,但到漢末魏晉,漸漸以藝術家的主體意志為藝術品的本源,如東漢蔡邕其<筆論>已言:「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山中佳兔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認為唯有主體的情志處在自由的狀態下充份表
現,才能成就書法藝術。這種自由情志主體的覺醒,成為魏晉藝術自覺的最大動力。而曹丕的文氣論就是這種思潮的結晶。 曹丕的文氣論也肯定天才之實有與命定性。不過與西方浪漫主義重表現個體天才的藝術論相較,中國藝術論更加重視才與學的辯證關係,而不強調一種非理性的天才,所以《文心雕龍》修正曹丕文氣論的天才宿命論說:「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現,蓋沿隱以至顯,因內以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學有淺深,習有雅正,並情性所爍,陶染所鈞。是以筆區雲詭,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深淺,未聞乖其學;體式雅正,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體性篇>)而宋代嚴
羽在討論詩學時也說:「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這種重視主體才質在藝術中的主導作用卻又不廢學養功夫的觀念,成為中國藝術論有別西方表現理論最大的特質。 這種重主體性的藝術觀念源於中國哲學強調主體性的特質。藝術思想由哲學思想發展而來,此在中西藝術思想史皆然。西方美學發展伊始乃以模仿說為主流,模仿說的重心在客體世界,因此重視藝術主體人格的思想,在西方出現得很晚,而羅馬時代雖有朗吉弩斯的《論崇高》將「莊嚴偉大的思想」、「強烈而激動的感情」視為構成崇高風格的主要因素,但朗氏的學說在浪漫主義時期之前並未受到重視,西方傳統藝術論一直
是以模仿論為主流 ,所重視的是藝術的技術與法則。這種主體性與客體性的強調不只是中西兩種哲學型態,更是兩種不同的藝術思想性格。 中國重主體性的藝術精神傳統,可以追溯自先秦儒、道兩家的思想。儒家往往將個體的真實德性視為藝術的本源,而在天人合一的思維下,主體之德乃是來自宇宙之道,因此「原道」乃成為中國藝術思想的重要核心觀念。而道家雖然對人性的本質看法與儒家不同,但將主體真實之德及德之所從出的道體視為萬有之本質的看法則與儒家無異,而藝術既是萬有之一,因此視德性與道體為藝術的本源。藝術被視為道體的自然呈現,成為中國傳統藝術論最重要的觀念,因此人格即文格,文如其人,乃成中國藝術之主
流思想,而既然天人合一,人格之真來自道體之真,則人格之表現即道體之再現,表現、再現不二,人文、天文,人心、天心為一的原道、原人觀念,乃成為中國藝術思想最鮮明的特質,而且有其一貫性,與西方主客對峙、表現再現分離、客觀主義美學與主觀主義美學爭論不休的情況恰為兩種不同文化傳統。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在<傳統和個人的才能>曾說:「每一個國民,每一個民族,不僅僅在創造方面,在批評方面也都有各自獨具的精神傾向。」 艾略特的文學批評可見出十九世紀哲學強調民族性的影子,所謂的「民族性」乃是認為人類的心靈在文化的各層面,諸如文學、藝術、哲學、審美觀、世界觀、價值
觀等,皆有結構化的傾向,各民族這些的思想常常是一「整體性」的「表現」,而顯現出其獨具的文化性格。 我們可以說重視人的道德主體性就是我們的民族性,而這種民族性乃是奠基於先秦儒、道兩家哲學。至於魏晉時代,由於才性主體及情感主體的覺醒,因此藝術論的本源由傳統的德性中心論,一轉而為才性與情感中心論。而魏晉玄學的核心觀念則是來自老莊思想,因此視道為萬有之本的觀念亦為其核心思想,道的本質就是無,也就是無限的有,也就是自然,也就是真,因此一種追求無限玄遠、自然任真的藝術思想於焉興起,這種玄心、玄風乃成為魏晉人格美的核心內涵,才性、情感與玄風遂成為魏晉藝術精神的主體內涵。
在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惟下,人的主體人格,不論是道德理性人格或才性氣質人格,都是與整個宇宙的本質貫而為一的,這種天人合一思惟下的藝術主體人格論與西方浪漫主義以降的「表現說」並不盡然相同。儒、道皆視人的內在本質與整個宇宙本質是同出一源,主體真實生命的表現就是宇宙生命本質的再現,中國傳統哲學都重視一種實踐的存有論,宇宙的絕對的真實乃是出於生命的存在實踐體悟,透過這種存在的實踐,終極的實在才能呈現出來,如《莊子》所言「其德甚真」(<大宗師>),才能「極物之真」(<天道>)。儒、道所謂的「真」乃是主體、客體合一之真,透過修養後所呈現的主體真實性,也是客體真實性的呈現,道心、天心一體呈現,主客不
二,物我合一。 因此,中國藝術論中幾乎沒有美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爭辯,中國傳統藝術精神自始即奠基於這種主客不二、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哲學性格,這種藝術精神不是主觀主義,也不是客觀主義,可以名之為「境界型態的藝術精神」。道家境界型態的哲學精神,在魏晉玄學發揮得更加徹底。魏晉玄學因「體無」所開出的觀物哲學,可以說把中國境界型態的哲學特質發展得淋漓盡致,在「虛靜玄覽」、「無心玄感」、「無我以應物」的審美觀照下,宇宙的終極實在就能呈現於人的心目之前,而此終極實在與人的內在之真性,乃是同出一源,因此表現了人的真性,就是再現了宇宙的最高實在,「與天合德,體道大通」 ,此即魏晉玄學
自然思想之核心精神。魏晉玄學奠基於王弼,而在郭象《莊子注》達到理論巔峰,錢穆先生曾說:「俟有郭象之說,而後道家之言自然乃是到達一深邃圓密之境界。後之人乃不復能深邃圓密之境界。後之人乃不復能駕出其上而別有增勝。故雖謂中國思想中之自然主義實成立於郭象之手,亦無不可也。」 「自然」成為中國哲學與藝術思想最重要的觀念,實是成立於魏晉。魏晉所謂的「自然」乃是貫通天人之真立論:「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 、「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 、「知天人之所為,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眾玄同」 、「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
在道家思想中,「道」、「自然」、「天然」、「真」、「素」、「朴(樸)」可視為同義詞,「自然」、「天然」、「真」、「素」、「樸」乃是作為道體性質的指涉語,也被視為人性的本質,「自然任真」、「平淡素樸」被視為人格美的最高境界,而成為後代審美理想的最高境界。 魏晉玄學的自然思想容有本體論之歧異,但這種自然思想透過無心以應物的直覺觀念,皆追求物我合一、心物不離的玄境,而自然任真乃成為人格美的核心價值。這種玄學精神就是一種藝術精神,一種審美的心靈。這種自然思想又進一步影響當時的人格審美觀及繼起的山水詩、山水畫所蘊涵的藝術思想及文學理論,「自然」成為美的最高標準。又因為不同的人對
自然與個體真性的內涵有不同的體會,因此玄學思潮與當時的才性論及情感主體的人性論就在「自然」思潮下有了溝通之處,而彼此互相影響;這種自然任真的人格論與當時的才性、情感主體自覺的風潮相結合,士人表現自我獨特個性情感姿態的審美風潮更為熾烈,後人所謂的「魏晉風度」 乃建立在此強烈追求自然任真的人格理想上。 魏晉玄學把自然任真視為人格美的核心價值,這種玄學人格在陶淵明的詩歌中具體實現為一種藝術的典型,陶淵明的人格與詩歌本身就是魏晉玄學所追求理想人格的實現。魏晉玄學才士一方面嚮往極高超、極自由的人格境界,但其人格與行徑不是「為人淺而不識物情」, 就是「為人薄行」 ,他們的哲學雖然亦強調
實踐性的重要,但最後卻往往流於「戲論」,無法落實於生命實踐中,而陶淵明則把玄學追求的理想人格變成具體真實的生命典型,所以朱熹才會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陶淵明去世後,蕭統撰<陶淵明傳> 表達他對這位偉大詩人的推崇,說陶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說明陶淵明的詩文乃其人格最真實的流露,文如其人,「真」字成為後世評論淵明其人其詩的最高評價。魏晉玄學名士哲學與人格實踐有隔、言行不一的問題,在陶淵明身上得到解決,陶淵明用他的詩歌、他的生命實踐了魏晉玄學
所追求的自然任真人格及藝術典範,而「自然任真」這四個字也成為陶淵明千古以來的定評,明代焦竑就說:「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懷得失,每念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陶靖節先生集序》) 「任真推分」即為玄學人格的核心觀念,「忘懷得失」即是玄學所追求非功利的玄心境界,而「天際真人」正是魏晉人物品鑒語中用以賞譽人格美的最高「題目」,《世說新語》就載:「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在北牖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意。』。」(<容止>)因此,我們不能夠把陶淵明當成那個時代的特異現象,陶淵明當然有他特殊的稟賦與生命涵養,但是他也深受那個時代文化的影響,他的人格與詩歌
正是魏晉時代精神的精純結晶,正要擺在魏晉的文化背景、哲學思潮、藝術思潮下,才能真正彰顯出他的時代意義。 魏晉藝術自覺乃是透過人性論與價值論的轉變而發生的,魏晉士人透過藝術追求某種人生的境界,也是透過藝術形式表達了他們對生命的感受與存在的省思,藝術是作為他們生命的感性形式表現而確立其價值的。所謂的藝術自覺其實就是生命覺醒的產物,因此可以說魏晉藝術仍與先秦生命美學一脈相承,藝術的核心就是人。 西方美學的觀物哲學乃是為知識求根據的思辨產物,而中國哲學所追求的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乃是為了安頓生命,瞭解生命真正的本質與歸宿,因此這種境界乃是超越語言而訴諸實踐,而其關鍵則在主體心靈的
修養上,因此重視主體人格的真實感悟恰為中國藝術哲學的主流。這種主體性的藝術論特質,恰與西方美學重客體、現象之真實鮮明對照,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文化性格。中國傳統思想所謂「真」往往是就主體體證感悟而言,因此「真」往往是「誠」的同義語,與西方注重客體客觀規律、原理法則、邏輯形式之真,表現了中西文化一重主體性與一重客體性,一重實踐性而一重分析性的區別。西方哲學所謂的客觀性是建立在主、客分離的二元思惟上,強調純粹就客體的性質結構加以分析,而不涉及主體個人的主體意識;而中國哲學之主流,則本天人合一、主客不二的思惟,認為唯有訴諸主體內在真實的體悟,才能真正突破客體之表象,瞭解其本質,因此所謂主體之真,反而是讓
客體之真能呈現出來的基本要件。在中國哲學中,並不強調天與人、物與心、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衝突,而是將之視為同構共應的和諧體,因此西方那種表現與模仿、主體與客體、物與心、靈與肉對立的二元思想,幾乎很少在中國思想史出現。 中國藝術思想的核心精神就是重視主體性,認為主體人格、情感、意志才是藝術的本源,因此所謂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判,常決定於作品是否出於作者真實人格的流露,這個條件被視為藝術之所以成立的必要條件,借用西方哲學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本質主義的假設,強調本質的優位性,作者的創作意圖及心靈主體內涵成為藝術的本源。 如果我們對「藝術」的定義採一個較為全面的看法,
自可顧及作者、作品、讀者及宇宙四個要素之間的關係來立論 。問題是這幾個要素雖然彼此可能互相影響,也對藝術產生不同的意義,但總有個先後的順序;藝術作品產生根源的第一序,總是在藝術家本身對其所在世界的反應,或借用現代學術術語──對世界的詮釋,及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動機上。本論文之所以名之為《論魏晉藝術精神的內涵與發展》,即著眼在藝術產生順序的邏輯推演研究,不管是藝術家對世界的反應或是藝術家的創作意圖與動機(無論再現或表現)都是一種精神的活動,因此藝術精神可說是藝術的源頭。 本論文即研究這種主體性的哲學思想在魏晉時代的變化發展,及這種哲學思想與價值觀如何引導當時士人生命行為及情
感反應,士人生命結構產生如何的變化,及此變化對當時藝術發展的影響。本論文將由才性主體、情感主體及玄風文化三個角度切入,呈現出魏晉時代士人對生命本質內涵的理解,及士人在面對漢末以來王綱解紐、儒學衰頹、戰亂不斷所產生的價值危機的情況下,如何重思生命的意義與理想人格的內涵,這種存在意義的反思理解深深影響到士人生命的自我形塑及行為表現,也就深深影響到當時藝術思想的發展,甚至對往後中國士階層生命價值、審美趣味、生活理想及整個藝術的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人類一切的文化就是人類生命自我追尋與形塑的過程,藝術即作者透過某種符號訴說他對生命的瞭解與存在意義的追尋。一切文化的根源總要回到生命本身,回到人的身上,人才
是一切文化的根源。因此,作者希望本論文的研究不只是客觀資料的呈現,也是生命真實的存在重現,是生命對生命,心靈對心靈,希望能入乎魏晉藝術精神的核心,亦能出於其外,透過現代語言,重新理解魏晉藝術所表現的心靈史、人格精神及人類對自我存在追尋的某個歷史過程。
想知道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更多一定要看下面主題
西方個人主義 對 什麼 是 理想 人生的的網路口碑排行榜
-
#1.钱穆先生:中国的人文修养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也非 ...
并不是有了我此身,即算是有我,应该是具有了我之此心性,才始成为我。此种我则并非西方个人主义者之超绝的理想我,而是中国人伦观中所得出的中庸的 ... 於 www.sohu.com -
#2.西方思想家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考评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 对西方思想家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 ... 西方伦理、 政治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 在其主导性倾向上, 是企求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於 www.zjujournals.com -
#3.【社会思潮】个人主义思潮的西方源流——《论个人主义思潮》随札(2)
在社会思想领域,有句口号叫“言必称希腊”。意思是,凡是有点年头的思想理论,往往会追溯到古希腊。个人主义思潮也不例外。 个人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发展可以分为古希腊 ... 於 www.jianshu.com -
#4.人生哲學講義
2.8啟蒙運動時期的人生哲學:接受了不少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見解,主張人性 ... 中國人的祭天、西方人的宗教禮儀)求與天達成溝通;基本上說神對人是全知的,而人對天 ... 於 scholar.fju.edu.tw -
#5.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
倘以上述各點對比於西方自由主義之重視消極自由、個人主義、低度政府及權力制衡等,則不難看出中國傳統文化是如何發揮其制約作用,使得知識分子對所吸收的西方思想加以 ... 於 www.edb.gov.hk -
#6.東西方心理思維之大不同
研究結果驚人地揭示了地理環境對人類思考推理、行為舉止和自我意識的影響。 ... 當被問及有關態度和行為的問題時,生活在更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的 ... 於 www.bbc.com -
#7.陳來:從中西比較認識中華獨特價值觀
現代西方自由主義道德的中心原則是個人權利優先,主張人人有權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從事活動,認為以一種共同的善的觀念要求所有公民是違背基本個人自由的。而 ... 於 theory.people.com.cn -
#8.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它是指對在世人生的一種看法與思想的方式,重要原則是個人主義與主觀,談 ... 因其與理想主義思想有相當關係,尤其是德國的存在主義,帶有濃厚的理性 ... 於 edu-exam-note.blogspot.com -
#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
作者先對以往有關華人道德思維的研究做後設理論分析,然後從倫理學的觀點,判定 ... 個人主義」代表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文化理想;「集體主義」是他們對非西方 ... 於 www.psy.com.tw -
#10.世俗化與人文主義 - FCNABC - 信友堂歡迎您
當他問道:基督教社會的理想在今天切合實際嗎?人數微少的基督徒試圖使大眾生活符合神的律法是合理的嗎?這時他是在試圖喚醒沉睡的西方基督徒 ... 於 www.fcnabc.org -
#11.《这才是中国:中国不是集体主义?西方不是个人主义吗?》
因此个人解放最终是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乃至于人类解放的高远理想汇成人的解放的大海。 爱爱老师《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的历史辩证法》文摘录:. 五四以来 ... 於 user.guancha.cn -
#12.信望愛── 徐敏雄專欄∕【論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社會服務 ...
至於新左派的批判主要是集中在資本主義體制本身的矛盾上,對他們來說,福利國家 ... 此外,志願部門也可以作為政府和個人之間的仲介團體,理想上,該組織的財物與行動 ... 於 www.fhl.net -
#13.美國個人主義的轉變─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
個人 自覺對美國歷史的推動極為重要。美國獨立之前,個人是從神. 權、封建制度與政府統治等三種勢力下解放出來,釋放的動力在於人的. 於 ir.niu.edu.tw -
#14.论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
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是漱石文学的思想核心,它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充满了明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气息,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同时,对明治社会在吸收西方文化时出现的两 ... 於 cglhub.com -
#15.个人主义- 抖音百科
个人主义是 一种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强调自我支配的政治、伦理学说和社会哲学。 ... 换言之,在西方社会的文明进程中,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生观和 ... 於 www.baike.com -
#16.【教育哲學與教育人物】
問,是教育學理基礎學科之一,西方兩大派別為理想主義和實在主義。 ... 個人是對整體情境作反應,心裡歷程不能分析為細小單位的聯結,「全體大於部分之總. 於 cte.utaipei.edu.tw -
#17.自掃門前雪」的個人主義,最終會破壞美國推崇的公民社會
(1)聖經傳統:源自基督宗教,崇敬上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2)共和傳統:源自古希臘羅馬,現代西方民主社會的基石,重視公民道德、公共參與。 (3 ... 於 m.facebook.com -
#18.疫情下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之殤
看到美國等奉行「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卻對此持 ... 由主義)是其主流範式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歷 ...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自由主義文化危機;個人. 主義;西方 ... 於 crrs.org -
#19.梁漱溟的生生思想及其對西方理性主義的批判(1915-1923)
如何在中西文化的激盪中尋得出路,並融合創造出更理想的文明,不僅是當時的首要課題,也是我們今日仍必須探討的根本性問題。 就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近代有關中國思想史的 ... 於 sites.google.com -
#20.西方哲學之旅:啟發人生的120位哲學家、穿越2600年的心靈 ...
本著作是哲普作品,也是西方哲學簡史,清楚表述哲學家在愛智過程中所領悟的心得,與對現代人生的啟發,綜合哲學家用生命驗證的成果,展示西方的核心理念,讓我們在品味 ... 於 bookzone.cwgv.com.tw -
#21.華醫學報- 第50 期- 2019年6月頁數1-15
想傳播之時,以傳統儒家思想為基礎,來對西方個人主義與個體性進行詮釋與轉化, ... 杜威(John Dewey)是聞名世界的哲學家,對於源自於西方世界的個人主義,當. 然有其論述。 於 tpl.ncl.edu.tw -
#22.失序的心靈: 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境
過度的個人主義會讓我們不斷退縮回小圈子,呈現某種疏離和孤立的狀態,不問世事,不關心公共議題,不看重傳統的信念價值,比如重視家庭、守望社區、忠於國家。那本書理想的 ... 於 www.eslite.com -
#23.導言:中國生命倫理學—— 在西方發生文化危機之際
在西方生命倫理學大家中,他是少數幾位能夠對現代西方文明. 進行清醒而深入的批判性反思的人。 ... 等”權利,實際上是在放縱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把國民經濟. 於 ejournals.lib.hkbu.edu.hk -
#24.刘擎:现代社会陷入了相对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主义的歧途
尼采指称的“末人”(last man)则是现代文明没落的最低点,他们除了“可怜 ... 面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困境,西方思想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也从未停息,但泰勒 ... 於 m.thepaper.cn -
#25.個人主義:加拿大生活中的最大疑問之一
事實上,人們一旦目睹過了暴力行為,已經很難在那幅畫面中再看到那些人的思想和理想,從而也沒有了更多的興趣去瞭解。 「反正事情是發生在畫面的那邊,不 ... 於 laoniaoji.net -
#26.老子與柏林─自化與自由的對比
又各自具有東方集體思維與西方個人主義的差異,也由此延伸出不同. 的政治、人生主張。老子與柏林,都在社會動盪中沉思,面對大動盪、. 大變革的時代,思考秩序、制度與 ... 於 www.cl.ntpu.edu.tw -
#27.心理衡論- 青少年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價值的問題還是思考的 ...
引人深思的是,台灣青少年一方面在價值觀上比成年人更社會取向、比西方同儕更道德 ... 上是相當道德取向的,也比較具有理想性,為什麼我們對青少年文化的整體印象卻是 ... 於 www.fgu.edu.tw -
#28.宣教好讀|跨文化宣教須知,「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Triandis是心理學科班出身,加上自身豐富經驗,對文化差異的深度理解和細微觀察,被譽為跨文化心理學之父 ,其理論為研究跨文化溝通者的經典必讀,大師在 ... 於 vocus.cc -
#29.人生的意義
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思考的。 ... 在今日的香港社會來說,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比較接近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即注意力比較集中於對富裕社會 ... 於 res.hkedcity.net -
#30.個人主義-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個人主義 (英語:Individualism)是強調個人內在價值的道德立場、政治哲學、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 個人主義提倡個人(生涯)目標和願望的實現,重視(個人思想與 ... 於 zh.wikipedia.org -
#31.英國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建設思想來源、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英國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建設思想,即英國一些思想家在描述理想社會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論,其核心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對未來美好 ... 於 www.dswxyjy.org.cn -
#32.第一節、幸福感與相關理論
「親. 親原則」有人類演化上的基礎,但是在西方受到個人主義的影響,西方文. 化對此有所壓制;然而,在中國的文化中,上層結構(儒家思想)與下層. 結構(精耕農業所產生之 ... 於 nccur.lib.nccu.edu.tw -
#33.現代死亡的政治
後現代主義對普遍性(universality)的攻擊看來是有點 ... Ariès認為西方個人主義在12世紀即已經出現,死亡的個人主義成. 份則來自宗教審判對個人罪業的自我承受,由此 ... 於 sex.ncu.edu.tw -
#34.失序的心靈: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境(Traditional Chinese ...
個人主義 為何會毀壞公民社會? 1830年代,法國社會哲學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對美國人的「個人主義」提出非常敏銳 ... 於 www.amazon.com -
#35.失序的心靈
(2)共和傳統:源自古希臘羅馬,現代西方民主社會的基石,重視公民道德、公共參與。 (3)功利個人主義:追求自己和自己親近的人的最大利益,例如賺取財富、享受人生、為 ... 於 philomedium.com -
#36.出題老師請將學生撰寫應注意事項於此註記
試述儒家對理想人生的主張。 試述西方個人主義對什麼是理想人生的主張。 試述個人對理想人生選擇的預設及背景。 試述個人主義的可能缺陷。 於 campusfms.nou.edu.tw -
#37.學會文獻-從中華智慧看香港政情
數十年西方教育的熏陶,使我們醉心於追尋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尤其是目睹中國百年來的 ... 鑒古而知今,若能多體會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歷史教訓,對我們洞悉今天的香港政情, ... 於 www.cwmhk.org -
#38.股市概念(166)~操盤手對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應有的認識
一個國家的治理,也應該是如此和諧,君王以道德治國,順天應時,而道德也是從天地間的自然化育而成。 這種人生觀並沒有大錯,但卻顯得太早熟。 西洋的古典繪畫中,很多都是 ... 於 m.wearn.com -
#39.杜威(John Dewey)與蔣夢麟的個人主義和個體性觀點
但西方的. 個人主義不只限於政治層面,也包含道德、哲學、宗教與經濟層面的個人主義,每一. 個人均被視為獨立的個體,被認為是一主體,因而個人主義的相對面即為「集體主義 ... 於 gec.hwai.edu.tw -
#40.個人主義_百度百科
個人主義是 一種強調個人自由、個人利益,強調自我支配的政治、倫理學説和社會哲學。從事實的本質上來説,是一種從個人至上出發,以個人為中心來看待世界、看待社會和 ... 於 baike.baidu.hk -
#41.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对立
因此,中西方. 人生观的差异,其深层次上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哲. 学理论体系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 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人生哲学理论基础问题的重. 大差异 ... 於 course.sdu.edu.cn -
#42.構建「華人本土心理學」如何可能之路徑辨析與解題
一、突破把心理學狹隘地理解為西方心理學,華人本土心理學才是可能的 ... 生之道,最終達到個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進而使個人即使面對人生的種種困厄也. 於 jicp.heart.net.tw -
#43.一個人更自由!「獨活」4種準備
面對人生下半場「獨活」考驗提前4種準備無煩惱. 陳炳辰認為,隨著西方個人主義盛行,加上個人經濟條件得以獨立,使得「獨居」風潮興起,無論歷經 ... 於 tw.news.yahoo.com -
#44.世上最好的職業:成為理想主義者 - New Acropolis
那麼,什麼樣的職業對我們來說才是最好的呢? ... 讓你人生的首要目標是去追循一個理想,超越所有的個人動機與興趣愛好,這就是我們邀請你考慮的職業 ... 於 www.acropolis.org.tw -
#45.在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 ...
同體;他們是如何處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這些在自由主義看來是互相對 ... 俗文化而建構的,在西方現代性脈絡中,民族主義是與自由民主同等的政治正. 當性原則。5. 於 tjeas.ciss.ntnu.edu.tw -
#46.哲學是什麼? 傅佩榮
所謂的「練習死亡」,是要練習減少身體的控制程度,亦即要讓身體的惰性無法對個人產生影響力,就好像死亡一樣。如此,才能讓心靈自由地追求智慧。 西方強調「愛好智慧」是 ... 於 www.swsh.ntpc.edu.tw -
#47.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政治逻辑之间分歧有多严重?
加强有关中西方权利思想的语境问题的理论思考,有助于对中西方政治生活与政治方式 ... 首先,西方霍布斯哲学本体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是与这样一个观念相联系的,即 ... 於 smthe.tsinghuajournals.com -
#48.Charles Taylor 對自由與權利觀的省思及其對人權教育的啟示
Taylor 認為本真性理想是現代西方. 人生觀的核心,他也抱持肯定態度。原子式自由主義也同樣蘊含這種理想,只不過它. 的「自我」觀過於狹隘(Taylor)。由於堅持個人的 ... 於 jepr.ntue.edu.tw -
#49.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自由主義與民權主義之比較分析
權力對貧富不均現況進行調整,否則自由主義的理想永遠是空中樓閣。二十世紀. 的自由主義轉而主張政府 ... 依據天賦人權與社會契約的觀念,人生而自由平等,非國家可. 於 www.fhk.ndu.edu.tw -
#50.為何西方人開始討厭市場經濟
個人 的行動追逐個人利益,本身這個行動. 促成市場經濟的主體並不是一個美德,相反這是. 一種惡。 然而,傳統的道德要求人們自我犧牲、. 為他人服務,這與市場邏輯衝突. 在 ... 於 strongwindhk.com -
#51.為孩子做「最好」的選擇?風險、理性選擇與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作者按:這是第三次以媽媽的身份為巷仔口寫 ... 個人主義對個人自主性(個人有能力選擇他要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的 ... 於 twstreetcorner.org -
#52.胡伯項:增強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文化底蘊
增強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底蘊,是黨執政經驗的深刻總結 ... 在這些西方政治思潮的影響下,一些人開始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發生 ... 於 www.nopss.gov.cn -
#53.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與儒家思維的比較
西方. 的文化則強調個體自主性與人權的保障,對個體有著高度的尊重,主張自由競. 爭與創新等。所以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是有著顯著的差異,當雙方遇到時. 容易產生強大的 ... 於 yihching.org.tw -
#54.从文学的视角看美国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这两种思想都是人的社会属性的. 派生物。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 邦》对人类共同存在的集体主义都 ... 於 library.ttcdw.com -
#55.美国文化的精髓——个人主义
法国自由主义者也谈个人主义,但把它看作是对国家干预最少而政治自由度 ... 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体为本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但唯有在美国文化中, ... 於 huazaikai730.blogspot.com -
#56.自由主義:
自十七世紀古典自由主義理論首航以來,現代西方社會所成就的社會、政治、道德及經濟等 ... 競爭式的個人主義(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 自由價值的首要優位 ... 於 soc.thu.edu.tw -
#57.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五章 - Wikisource
機械實在是近世界的惡魔但他所以發現的則為西方人持那種人生態度之故。 ... 我們觀於近世西方文化其精神方面理智之發達其與社會上個人主義之發達則知 ... 於 wikisource.org -
#58.我們是不是可以換一個腦袋來想幸福感?
一種對人生感到滿意、快樂的感覺 ... 如果東方人追求平靜是理想情緒狀態,那他們還會在這根量尺線 ... 跨文化研究成果:集體主義/個人主義;互依自我/獨立自我;低. 於 www.indigpsych.org -
#59.【紀念五四百年】五四前後的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的基本主旨是不依賴上層政治的改良,積極尋求從底層入手促成民眾日常生活 ... 而西方的自治觀念卻來源於對個人權利的充分尊重,「自治」是 ... 於 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 -
#60.得涂爾幹的家庭。在這容易受到他「他有一種篇而且由於
另外一點,他所. 處的知識背景剛好是在西方所謂理性. 主義跟科學主義興起的這樣一個背景 。 我們知道在伽俐略革命之前,一. 般對宇宙的解釋通常是訴諸於聖經,. 於 ir.csmu.edu.tw -
#61.昆蟲-熱血漢奸劉曉波.doc
台灣、日本的人權問題表示解決,香港解決了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是功利化的,它爭取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權利,但現代存在主義哲學追求的則是生命意義上的個性解入,這是一種“純 ... 於 docs.google.com -
#62.論梁漱溟對西方法津的理解
實根據——法是服務人生而熨貼人心. 的生活樣法。 ... 個人主義、權利思想,成就了現代的. 西方社會,這是對於中世社會的反動 ... 巧,但從中國儒者的理想的眼光看來,. 於 www.cuhk.edu.hk -
#63.论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与超越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有译“普世主义”)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个一以贯之的显著特征。 ... 第一个层次属于规范层次, 它构成了一系列个人主义的理想, 如个人的价值和安全, ... 於 www.globethics.net -
#64.對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溝通的認識
个人主義是 自由主義的基礎和出發點,是其根本的特徵和原則,是它區別於其它一切政治學説的 ... 對自由主義來説,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強制所能施加的恰當對象。 於 www.dharma-academy.org -
#65.個人主義- 最新文章
個人主義 (英語:Individualism)是強調個人內在價值的道德立場、政治哲學、意識形態 ... 《西方文化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世界》:最「WEIRD」的人,才能主導世界! 於 www.thenewslens.com -
#66.西方人眼中的个人主义
[关键词]西方,美国,个人主义 ... 解”:“首先, 它指带有人人权利平等的理想主义学说, ... 尔在谈论个人主义时把它看作是对国家干预最少而政治. 於 core.ac.uk -
#67.「個人主義」的翻譯問題:從嚴復談起
我們西方人必須避免假設我們所擁抱的理想是能顯示「真正的自我」. (authentic self)的唯一方式。我們大多數的人所肯定的方式,是現代西方傳. 統所建構的自我:強調隱私;對 ... 於 www.mh.sinica.edu.tw -
#68.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consumerism)消費主義是指人們一種毫無顧忌、毫無節制的消耗物質財富和自然資源,並把消費看作是人生最高目的的消費觀和價值觀。”消費主義表現在“對物質產品 ... 於 wiki.mbalib.com -
#69.個人主義 - 奮起
我們早該擺脫西方的思想殖民,以慎思明辨拆解自由平等的口號。不幸的是,雷根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卻走在回頭路上,明顯加劇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1980全美前1 ... 於 rise-tw.org -
#70.梅寧華:實現中國文化新的歷史超越(2)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靈魂的西方文化,已難以適應當今全球化時代的社會發展要求和趨勢。可以說,當今西方社會出現的問題實際上是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斷層造成 ... 於 www.nopss.gov.cn -
#71.華人雙文化自我的個體發展階段: 理論建構的嘗試*
逐漸形成西方現代工商社會中的若干心理與行為特徵,合而成為一種兼具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雙文化自我。本文 ... 論,個人主義取向的文化所衍生的則是偏向個人取向的. 於 myweb.scu.edu.tw -
#72.個人主義思潮的西方源流
文藝復興是對舊時代的精神反抗。進入十七世紀以後,資產階級開始從制度上對舊社會進行革命與重建。 這個時期,自由主義思想家接過文藝 ... 於 kknews.cc -
#73.東方和西方的思考方式根本差異在哪?
最明顯的差異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一般來說,西方人比較個人主義,來自印度、日本或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人比較有集體主義傾向。 於 www.cw.com.tw -
#74.张瑜: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与正确导向
在这次转型中,“告别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坚持“革命理想主义”的社会 ... 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印刷即民主”正是对印刷媒介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变革的一种刻画。 於 www.mkszyyj.net -
#75.失序的心靈: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境
至於作者貝拉心目中理想的公民與公民社會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追尋?作者認為仍可以透過教育重塑,改造美國文化,讓人們重拾道德責任,了解人生追尋的 ... 於 www.bookrep.com.tw -
#76.《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 讀後感
隨著心理學不同學派的核心主張,我又逐漸對 ... 「人生的意義」是現在許多文學、戲劇、電影中會不時討論到 ... 基本上亞里斯多德的看法我是認同的,在西方個人. 主義、 ... 於 www-ws.gov.taipei -
#77.“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
【内容摘要】 苏敏自驾游的个案,一度引发社会公众对“为自己而活” ...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思潮传入中国 ... 於 www.tsyzm.com -
#78.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理特徵
在個人主義當道的西方社會中,自我問題是歐美心理學(特別. 是美國心理學)日益重視的研究課題。 ... Richard Coan(1974,1977)是少數不僅對理想人格進行統整. 於 web.ba.ntu.edu.tw -
#79.林语堂看《浮生六记》:边缘文化人的西方视角解读
他对芸爱美天性的赞赏,即是他理想的女子(妻子)形象;他对沈复夫妇情趣相投的赞赏, ... 从外部而言,他这种个人主义人生观,还与其生活环境对中国社会的疏离有关。 於 finance.sina.cn -
#80.失序的心靈: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境
我們對這社會仍有更多的責任與義務,人際孤立是現代社會遇到的普世困境,也是每位關心公共事務、社會責任的你我應該關注的課題。 喜歡這本的人,也看了... 於 readmoo.com -
#81.揮筆灑墨為所當為
人文主義對西方文明的意義;《人性的曙光》2的杜麗燕則. 以大量的思想文獻回顧如Hesiod ... 文主義以人,尤其是個人的 ... 中理想的人生以及荷馬時代獨特的英雄倫. 於 ntupoli.s3.amazonaws.com -
#82.失序的心靈: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境
由於沒有普遍的道德理想能判斷哪些衝突是能被解決的,人們唯有透過溝通才有機會解決分歧。「溝通不僅對男女關係至關重要,而且我個人認為,溝通是我們在 ... 於 www.cite.com.tw -
#83.失序的心靈: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境
1830年代,法國社會哲學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對美國人的「個人主義」提出非常敏銳的分析,他警告「只顧個人利益、自掃門前雪」的個人主義,最終會破壞美國 ... 於 www.books.com.tw -
#84.現代都市社會群己關係的再思
個人 、社會、國家都是西方近代的概念,傳統的中國沒有這種分法。儒家思 ... 西方學術界早期對理想社會的探討,包括了眾多的人文主義者論意志自由和. 於 www.cityu.edu.hk -
#85.西方人权观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吗
①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西方人权观体现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中国人权观更 ... 然而,即便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也对这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表示 ... 於 www.humanrights.cn -
#86.台灣地區民眾的個人主義、家族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及 ...
而西方的文化則強調對個體自主性與人權. 的保障,主張自由競爭及創新、民主等中心思想。因此,當中國文化遇到西方文. 化時,必然產生強大的衝擊。 而荷蘭社會心理學者 ... 於 nhuir.nhu.edu.tw -
#87.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
在他看来,西方近代以来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破碎了“作为整体的社会”,使个人与 ... 康帕内拉),作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钟声里萌发。 於 www.21bcr.com -
#88.新加坡和中國能為非西方民主走出一條新路嗎
對 所有個人平等權利的要求即使沒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達。在20世紀的各文明中,個人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顯著標志。與其他集體主義盛行的地方相比, ... 於 news.cnyes.com -
#89.西方哲學的人生理想|什麼是幸福和快樂?哲學經典小語
伊比鳩魯Aristippus 快樂主義. 「快樂」與「幸福」的分別; 西方古代對幸福的初步思考; 結論. 有關哲學 ... 於 mrsyangblog.com -
#90.孙凤武:究竟什么是个人主义?
到了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对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批评增多起来,那里的道德进步也加速了,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批评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文化人”的思想, ... 於 www.aisixiang.com -
#91.演說1211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理論
def「平等」意指社會對資源, 權力, 機會, 自由… ... def自由主義意指一種社會價值哲學, 認為個人的人生價值與規劃是一切價值中之最高者, 也是 ... 於 www.tangsbookclub.com -
#92.拒絕別人、做自己是好的,但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情緒表達抑制發揮比較負面的作用,可能會與消極情緒、社會焦慮、憂鬱症有關,甚至對心理彈性、社會適應、記憶等產生消極 ... 於 www.gvm.com.tw -
#93.中國自由主義的道路――林毓生的政治關懷與五四全盤性反 ...
標──「加深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內涵及其在制度上演變的理解」、「加. 深對現代中國歷史環境 ... 人生的. 目的是完成道德的自我;在社群中個人本身就是終極目的,他不可. 於 toaj.stpi.narl.org.tw -
#94.西方倫理思想
它的基本任務是解釋和論證聖經的道德觀念和倫理原則,注重個人對上帝的關係和靈魂拯救。它融合了東方宗教,極端強化了古希臘羅馬倫理思想中的神秘主義和禁慾主義,形成了 ... 於 www.jendow.com.tw -
#95.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何不同?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弊端。由于社会大部分物质生产力以资本的形式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而是少部分人、一部分国家的发展以大 ... 於 m.newsduan.com -
#96.何謂意識型態?所謂「自由主義」的主要內容有哪些?何以「 ...
自由主義是不是一種意識型態,不能僅憑一己之言,要提出學 ... (2)對理想政體的看法。 ... 自由主義者相信「人生而平等」,他們支持功績主義,認為個人. 於 www.ibrain.com.tw -
#97.227 失迷的學哲育教下「化代現」方西來年十三近
震盪是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的文明社會在科學方面有了空前的成就,連帶 ... 如果相信文化精神和教育攸關,便要對教育作一番檢討,尤其要對教育哲學做一番檢討,. 於 teric.naer.edu.tw